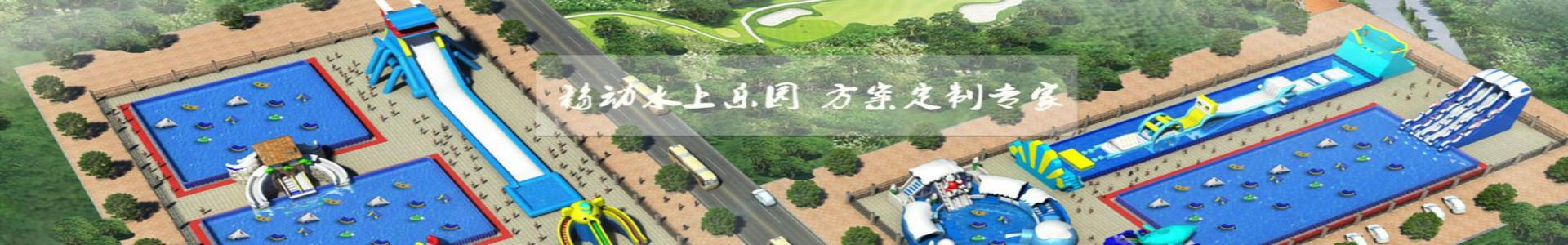《悬浮术》是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发展的一支文学幻想曲。陈崇正借助科幻元素,以令人惊奇的想象力探触人类未来,其中包含了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和科技反噬的隐忧,在轻盈的悬浮飞行背后是深沉的哲思。
通过陈崇正的小说,我们能够看到一个巨大隐秘的遥远的南方,如草木那样葱茏,但是里面包蕴了巨大的现代性和当下性,一方面反映出了大工业、大商业对现实的作用,也能看到他写出了南方之所以称为南方的那些长期主宰人们的思维方式。
小说交融着机器与人类、科技与现实、激情与异化、伦理与哲学等诸多复杂的纠结。这是一曲富有大湾区气质的科幻狂想曲,一次想象力的御风而行。历史连结着未来,浪漫交织着反思。小说启示着:科技既为大道,也是窄门。视科技为无条件的大道,则遁入疑难重重的时空;带着反思穿过科技的窄门,人类才能重遇生命的主体性。
元宇宙年代,随着人工智能的高速发展充气卡通人,戴友彬应运而生,他承载着上一代人寄托的浪漫梦想,既是故事采集师,也是梦境制造师。当更高文明出现,这个收割真实、虚构梦境的狩猎人,成了美人城集团与更高文明博弈的猎物,开始了实体虚拟人的一生。而他周围的人,主动或被动地进入悬浮状态,他们离开现实之土却也难达理想之地,或寻路无门充气卡通人,或陷入虚无,谁来拯救他们?谁能拯救他们?
陈崇正,广东潮州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硕士,现担任广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广州市文艺报刊社副社长;著有长篇小说《香蕉林密室》《美人城手记》,小说集《折叠术》《黑镜分身术》《半步村叙事》等;曾获广东有为文学奖、红棉文学奖、华语科幻文学大赛银奖等奖项;入选广东省青年文化英才。
几乎每天曲灵都是最后一个离开办公室,习惯性的加班让她感觉自己就像商场门口巨大的充气卡通人,勉强撑大,空虚而笨拙。出版行业日薄西山,基本都靠教材教辅勉强支撑。很多人都劝她跳槽,她也不是没想过,只是不知道自己除了当图书编辑,还能做些什么。
男孩戴友彬的电话是一个小小的意外。回到家她还十分兴奋地和丈夫范冰谈起这件事:“这小家伙还真是机智,他居然根据我们出版的那本《大数学天天小练习》封底上面附的联系电话,找我这个责任编辑来要答案!那本练习题是最新的,网上找不到,他们老师非常黑心,把后面附的答案都撕了,然后自己私下办补习班,答案只讲给参加补习的同学,那些不到老师家里补习的同学,做不出来就挨骂。我还是次碰到打出版社电话询问答案的学生。”
曲灵滔滔不绝地讲了她和那个学生的很多聊天细节,总之都在夸戴友彬聪明。范冰的眼睛一直都没有离开电脑屏幕上的姜太公网站,那里有他的大事业。他将妻子的这一席话,理解为又在含沙射影让他赶紧开枪造人。他们结婚三年,范冰都一直坚持先买了自己的房子再养孩子,但眼看房价又涨了,银行账户里的钱不但追不上首付的涨幅,有时还因为“姜太公”操作不当而亏钱。他知道曲灵喜欢孩子,但只能抚慰她,房子和孩子不可兼得,再忍忍。
范冰又一次耐心解释,姜太公网站是个投资计划,不是赌钱。范冰是这座城市里小有名气的股评家,股评写多了自己也信以为真,辞职专门在家炒股,业余写些教人如何炒股的书,销路还算不错。也因为图书出版的机会认识了曲灵,曲灵当时正处于父母频频逼婚的人生低谷,所以两人算是闪婚。范冰跟他的朋友们开玩笑说,结婚就像手机充电,接口对,插上就能充。这话有点黄,大家都笑。刚结婚那阵,他还信誓旦旦对曲灵说他很快就会重回职场,但后来身边的许多朋友都玩“姜太公”,他也迷上了,还发明了一套算法,据说能够在上面赢点小钱。
眼看着自己的丈夫从专家变成赌徒,曲灵眼中的光渐渐暗淡下来,她感到失望。她想养个孩子,但在她丈夫的算法里,养个孩子的成本不亚于供两套房子。问题在于,房价涨了又涨,他们现在既没有房子也没有孩子。
范冰说:“面包会有的,孩子也会有的。”但只是嘴上这么说,他现在连做爱都草草了事,姿势都不愿意换。曲灵抗议过,他就说:“手机充电,要那么多姿势做什么?”那个瞬间,曲灵心里闪过从她生命中走过的所有男人,有的握着她的手说对不起,有的轻轻吻了她的唇,有的在她耳边说起木棉花的白絮……所有的回忆都成为惩罚,将她重重地摔回现实里,身边是她丈夫连绵不绝的呼噜声。
戴友彬同学的电话终于来了。曲灵内心一阵舒畅,她在电话里逗他玩。这个小孩子,出乎意料地早熟。他索要答案,却不是全部答案,每次都会预留一点余地,故意错几道题,以此掩人耳目,制造一种靠实力完成的假象。曲灵笑他:“你还挺有心机的嘛!”“那当然,这不是心机,这叫聪明!”“我也学聪明了,每次只告诉你半个单元的答案。”戴友彬大呼小叫,各种扮可怜,说这样惨无人道充气卡通人。曲灵在电话这边微微笑了,在她心里,她只希望这个孩子能多打电话过来,仅此而已。这一段时间,只要加班到办公室只剩下她一个人的时候,她就会开始期待电话响起,期待戴友彬在电话那边用大惊小怪的语气对她说话充气卡通人。为了延长聊天的时间,她的答案也会附上各种条件,比如让戴友彬回答她的一个问题。重点不在于问题,而在于她希望他能跟她聊点什么。什么都行。
戴友彬对曲灵说:“曲阿姨,我在写小说,每天一两千字,预计毕业就能写完。”他又说:“到时您帮我印成书,我要是出名了不会忘记您的。”曲灵大笑。她不忍心告诉他,自己只是一个教辅材料的编辑,基本不做文学类的图书。
戴友彬对曲灵说:“阿姨,我班上有个女生很漂亮,跟您一样漂亮,她喜欢数独,有本书,我看也是你们家出版的,能不能也帮我找找答案?”曲灵还是大笑。“你怎么知道我很漂亮?”她这样反问道,却悲从中来不可断绝。时间倒退回十年前,她不是校花,也是年级的级花,没想到今天居然走到这地步,需要一个孩子来赞美她。而且,她发自内心喜欢这样的赞美,小孩天真的声音比任何一个臭男人的甜言蜜语更能令她心花怒放。
戴友彬又说:“我希望我爸爸不要再赌钱了,这样他就不用老是东藏西躲……”戴友彬的嘴巴刹车了,他没有再往下说。曲灵只能换个方式发问:“那么,你妈妈呢?她没有让你爸爸别赌钱吗?”戴友彬说:“我已经有八个月零十没有见到我妈妈了!”说完他哇哇大哭起来,那哭声如此悲伤,简直天地为之坍塌,以至于曲灵有点怀疑是不是假哭。但那声音却如此真切,撕心裂肺。曲灵安慰几句,她刚想问他“你妈妈是离开了还是去世了”,电话就挂断了,嘟嘟发出一串烦人的声音。
曲灵尝试回拨电话,电话没人接听,跟她之前尝试过的一样。这个问题在一个星期之后才有了答案。一个星期之后,戴友彬又来问答案,他说,他爸爸本来想停掉家里的电话,因为他自己有手机,是戴友彬苦苦哀求,才保住了这部电话。因为这是他和妈妈的联络方式。“妈妈跟别人跑了。”即便如此,戴友彬还是在等待。
“妈妈从来不会打过来,打过来也接不通。我爸怕追债的人打电话试探他在不在家,所以规定我每次打完电话,都得把电话线拔掉。每次都是我打给妈妈,但她并不是每次都接电话,有时候电话那边酒吧音乐的声音太吵,她听不到,有时候她接通了,就告诉我她现在没空,回头会打给我,但从来没有。”他这次没有哭,但声音很低,显然有点难过。曲灵突然萌发一股冲动,想跟这个孩子见见面。但戴友彬很警惕,支支吾吾拒绝了。
挂完电话,曲灵望着窗外的万家灯火,城市虚幻的夜景,公路上因为拥堵缓慢移动的车流,窗玻璃上倒映出她疲惫的脸。有那么一瞬间,她感觉自己像一株沙漠中缺水的植物,生命正在流逝枯萎,而她无能为力。
丈夫范冰在灯光昏暗的卧室里抽烟,门窗都没开,卧室里只有一个一明一灭的红点悬浮在空中,整个房间像个碉堡,呛人的烟味在这个有限的空间弥漫,仿佛刚刚经历过一场战争。毫无疑问,一定又输了钱。曲灵心里清楚,但什么也懒得跟他说了,她走过客厅时,伸手把电视打开了。电视里有一群企鹅正在跳水,主持人在旁边兴奋地说着什么。她径直走向房间,开了房间的灯,取了衣服走进卫生间,开始洗澡。温热的水从头顶喷下来,正在一寸一寸润湿这棵沙漠里的植物,让她蓬勃。这是中最为舒畅的时刻,内心的花朵正在一瓣一瓣打开。刚洗完头发,浴室里的灯突然熄灭了。卫生间并没有窗户,一种的黑暗封锁了周围的空气。“停电了吗?……别闹!”头发粘在脸上,眼睛都睁不开。浴室的门开了,丈夫在她身后,用一条浴巾帮她擦头发。记得刚结婚那会儿,他们一直会玩一个游戏,互相在对方洗澡的时候捣蛋关掉浴室的灯,直到对方求饶才开灯充气卡通人。“别闹!”她叫了一声,但身体却因为一只男人的手而不禁颤抖了一下,一种久违的情欲在身体里激荡,她感觉自己第二声“别闹”明显带着某种召唤。突然,丈夫用浴巾将她整个头都包住了,一手捏着她的脖子,一手把她的手扳到背后,然后她的手被他从背后扭在一起,咔嗒一声一副塑料手铐将她的手锁住了。“别闹!”她已经有点全身乏力,想到丈夫居然还准备了道具,看来是一场有准备的战争。
第二天她在床上醒来,丈夫就睡在她身边。她去抱他,才发现他额角上也有一道淤青,不禁笑了,看来昨天都玩过头了。她走出客厅,客厅果然一片狼藉,白色的浴巾和那根跳绳就扔在地板上,让她脑海里掠过一些画面,脸上不禁红了。好长时间没有脸红过。但地上没有塑料手铐。她看了看手上,果然被勒出一道青紫的痕,动一下背上也是痛的,两条腿也像昨天刚长跑过一样酸痛。昨晚并不是梦,她在内心暗暗确认。
她走进卫生间刷牙,发现脸上竟然有一块淤青。下手这么狠,居然打脸,怎么出去见人。洗完脸她开始做早餐,煎完荷包蛋,她将蛋壳带到卫生间,对着镜子给脸上的淤青涂上一点蛋清,心中盘算着该怎样跟同事解释脸上的淤青。就说撞到厨房的玻璃门上,幸好没破相。丈夫范冰也起床了,他如往日一样沉默,像条死鱼一样走进卫生间,撒了一泡尿,开始对着镜子刷牙。她坐在餐桌上等他洗漱完毕,一起喝稀饭。她希望他能看到她脸上的神采飞扬,但丈夫看上去疲惫至极充气卡通人,像个荒原。他话也极少,一点都不像昨天生龙活虎的样子。大概男人都这样,累了就不说话。吃完饭,他把一盒避孕药放在桌子上,再推到她面前,要她吃药。
“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这么快,说不定过几天小孩都由机场批量生产,按需分配,我们直接领养一个就完了。现在要孩子压力太大,听话,安全起见还是吃药吧,免得惹麻烦。”他说话有气无力,但显然没有离开桌子的意思,而是在等待,看着她把药吃下去。
她丈夫笑了,笑容真难看。在他转过身去倒水的间隙,她悄悄将药片换了。饭后吃避孕药的情节被她猜中了,一切都在意料之中。她暗自得意。
一夜疯狂居然让她整个星期都活力无限,心情愉悦,眉眼间都是笑意。办公室的死党都怀疑她最近有故事,揶揄她是不是有了婚外情。但这种好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有,她被丈夫抽烟的姿势吓出一身冷汗。她从来没注意她的丈夫范冰抽烟的时候,居然是用拇指和食指捏着烟嘴,抽一口就将烟头朝下拿着,左手做出一个OK 的手势。她观察了很久,就连他盯着姜太公网站十分专注在赌钱的时候也是如此,几乎从来不会将烟叼在嘴上一明一灭地抽。
假设是有另外一个人,那么,她的丈夫范冰,是否在家里看着呢?如果不在,或者他被打晕了,他又如何知道她需要避孕药?如果在一旁看着、听着,他为什么不报警?难道一个男人居然能够忍受这个?丈夫会不会像网络新闻说的那样私下交易将她卖了还债……范冰那张死鱼一样的脸重新在她眼前浮现。砰的一声,她一拳捶在办公室的桌子上,人都站了起来。旁边的同事全都看过来,她用了十几秒的时间才控制住自己的呼吸充气卡通人。她坐下来,旁边几个同事围过来,七嘴八舌让她别太累,别太拼命,建议她休个年假。她知道他们的意思,去年出版社已经有两三个人得了抑郁症辞职了,他们觉得她这个工作狂很快也会因为工作压力而疯掉了。
大概这就是欲哭无泪的感觉充气卡通人。不过仅仅靠一个拿烟的姿势,似乎也太过荒唐。既然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那么这件事就可以被处理为不存在。选择遗忘,这是曲灵能想到的对付这个难题的办法。
不过休个年假倒是一个好建议,她需要一点时间来想清楚后面的路。就在她正在考虑应去哪里旅行的时候,戴友彬的电话来了。这个男孩说,他想见她,想和她谈谈他差不多写完的长篇小说。她在他的语气中听到了一种恳求和焦灼。犹豫了一下,她说:“好吧,明天去,说地址。”她的话变得这么简短,这让电话那边的小男孩也同样迟疑了几秒钟,还是说了一个地址:白鹤路。曲灵在他的语气里捕捉到他的敏感,于是笑着说了几句无关紧要的话。曲灵知道白鹤路,在城北,很偏远的一个城中村。她一直想买房,偷偷也跑了几个楼盘,其中有一个就在白鹤路附近充气卡通人。出了地铁站,还得坐三十分钟的公交车。
“哦。拜拜,明天见。”戴友彬这个机灵鬼大概听出今天曲灵心情不佳,他电话挂得很快,估计都在电话那头吐了吐舌头。
曲灵给领导打了休年假的电话,说回来再补请假条。她是劳模充气卡通人,难得请假,领导满口答应,还客气地给她推荐了几个度假的好去处:“比如梯田,现在的油菜花应该就要开了。”她小心应付着领导的每句话,赔着笑,好不容易才结束这通电话,后悔刚才不应该打电话,发个短信可能更简单。
离开出版大楼,夜色中行人匆匆。地铁在这座城市的地底下奔跑,曲灵到了地铁口,却突然不想像以往那样钻进去。她选择一路向西,一个人走走。她跟自己说,得放空自己,舒缓压力,别胡思乱想,疑神疑鬼。她希望通过自我暗示来平和心绪。但这个时候,她却发现身后好像有人在盯着她看。她回头看,有个瘦而高的人站在树下点烟充气卡通人,也看着她。她吓了一跳,几乎是一路小跑走出了很远,看到一辆出租车停在路边,她打开车门钻进去,大叫了一声:“开车!”司机回头厌恶地看了她一眼,这才慢条斯理挂挡踩油门,把车开动。他用低沉的声音问:“要去哪?”她还能去哪里,她只能回家。
第二天醒来,世界依旧,机器人还没有发起攻击,窗外是另外一个完整的白天。这一夜睡得特别沉,整个睡眠都是实心的,像个罐头般密不透风,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想不起有什么梦,醒来只是觉得还想睡。
今天她要去见戴友彬小朋友,但奇怪的是,她再也找不到一个多月前的冲动,那种说不清楚的兴奋。难道是她身上有什么发生了改变?有什么东西错过了吗?她一个激灵从床上坐了起来充气卡通人!
在去白鹤路的路上,她在药店买了一支测孕棒。刚走出药店,她又掉头回去,她怕一支测不准,又买了一支其他牌子的。在药店外面的街边,她感到有点晕眩。大概只是紧张。但万一不是范冰的孩子呢?这是要干什么?她几乎要伸出手去扶住路边的电线杆,才瞥见电线杆上布满浓痰和鼻涕的痕迹,赶紧将手缩回来。世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变得如此细碎,像是一块玻璃上的裂痕,从隐隐约约到最后爬满了整块玻璃,似乎伸出一只手指去碰一碰,就会哗啦碎满一地。
她知道走过一个街角,就有一家麦当劳,红红火火的店面。麦当劳里面有洗手间。只需要十分钟,就能知道自己是否怀孕。如果是入室强奸,是否要保留证据,比如身上的伤痕?那天客厅里是一个人,两个人,还是三个人?接下来会吃什么东西都吐吗?她摇了摇头,拼命又摇了摇头,试图将这些想法摇出自己的脑袋。阳光似乎很刺眼,到处都透亮。她疾步向前走,将手里的两支测孕棒都扔进垃圾桶,拦了一辆出租车,前往白鹤路。